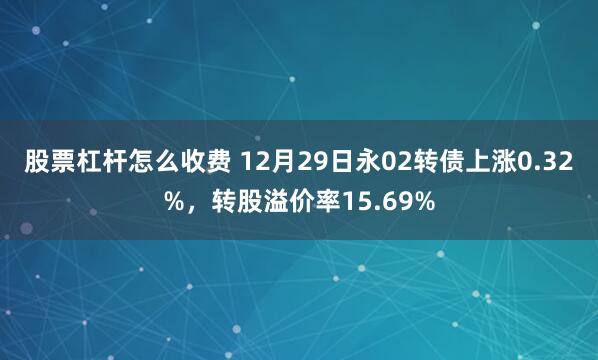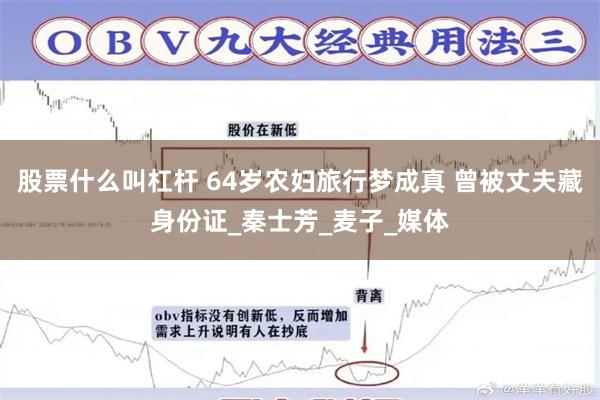
摘要:股票什么叫杠杆
手里只有5000块钱,出去转转需要花多少钱?大冰直播间,去年连麦到一位60多岁的女士,用质朴的声音讲出自己的愿望,“咱们农村嘛,种完麦子就往南走。搁云南,西双版纳那儿转转,过过冬天,怎么样?”
这句话让那晚的连线视频爆火,全网开始寻找这位「麦子阿姨」。她最终在河南安阳被找到。大冰为她安排了一趟旅程,实现了她的愿望。随后她上了春晚,接拍了一系列广告,被推向一个更大的世界。今年4月,她回到自己的村庄,回到自己的身份,一些东西被改变了。
文、视频|徐巧丽 编辑|陶若谷 剪辑|王婉霖
麦田顶流
大网红回来了。消息从南撵到北,传遍了西辛安村。
手机里都管村东头的秦士芳叫麦子阿姨。这不,搁云南旅游了四五个月,出去见了世面,人都变白了。她上地里干活,就有人问,玩得好不好?高不高兴?还有人问,你一个人出去四五个月怕不怕?她顶着油亮的颧骨,对这个问题不屑一顾,“我又不是大美女,又不是美男子,怕谁抢走我?”
大网红是坐轿车回来的,背了个白色蛇皮袋,除了两件棉袄,还装了一双西双版纳的拖鞋。有邻居拦下她,要拍个肩搭肩的视频,她马上对着镜头自我介绍,“你们好,我是麦子阿姨。”
没几天就有扛着摄像机的人往麦地里走。秦士芳回来第一件事,先下地看看麦子,出门时还没有一个手掌高,现在已经长到五六寸,绿油油的。野燕麦长得和小麦一样高了,她弯下腰拔掉杂草,旁边的摄像头就对准她。
人最多的属6月2号,收麦子的那天。上午秦士芳就在地里守着——十来家“媒体”跟她约了收麦子的拍摄,但收割机得一家一家排着来。直到下午2点,收麦子的农机轰隆隆碾过麦子地,摄像师也到齐了。
他们围在田埂上,拍大网红割麦子,拍她擦汗,拍她穿过麦田。几亩地半小时就割完了,素材不够,又追着收割机到别人家的麦地里拍。村里开着三轮车的,戴着草帽的,掀着肚皮的,都要停下看一看。
围观割麦子。讲述者供图
大网红一会儿对着县里的融媒体热情洋溢,“在外面打工的,来家收麦子啦。”又抱着麦穗对自媒体博主喜笑颜开,“丰收啦,大丰收”——没对镜头说的是,今年天旱,麦子减产了200斤。从走向西双版纳那天开始,生活不可避免地开始表演化。讲完了,拍她的人一个个走了,秦士芳又留下来捡了一会儿麦子。
地里的工序多,收完麦子,还要碾麦子,种玉米,种白菜、包菜。天气暖和了,该浇水施肥了,这个农忙季,拍摄没有停下来的时候。省里的记者,让她对着簸箕吹麦子。市里的就拍她吃馍馍,吃馍馍也要咬上一大口,拍出来才好看。秦士芳记下了,再对着镜头吃东西都咬上一大口。
拍得多了,秦士芳也琢磨过味儿来,“喜欢看我种地,也喜欢看我出去。”她回家后的生活也沿着这两个剧本展开。
6月底,我在玉米地里见到秦士芳,穿着花色上衣,上春晚染的栗色头发变成黄色,梳在脑后。地里的玉米长得齐腰高,除了施肥,不需要再做什么了。她为了照顾我,把施肥延后了两天,“怕你来了没活干,你不就没得拍了吗?”
第二天她带上我,早上5点半出门骑行拍视频——不是给村民看,是给粉丝看,“给那些身体条件不好,年龄大了,经济条件达不到,或者在家看孩子做饭任务重,想出去也出不去,没有条件出去的人看看。”
她买了一辆四五千块的电动自行车,配上骑行头盔,一副手套,经镇上的人介绍,加入了一个“飘姐骑行队”。
电动自行车以家为中心,续航里程120公里为半径,开到安阳的小南海水库,鹤壁的阿斗寨,邯郸的天下第一柏。骑行的景色,一一收纳进镜头里。回到家煮玉米、蒸馍馍,就让丈夫给她拍。她还加入了安阳新媒体网络名人协会,里面有大学生驻村书记、乡村网红。
秦士芳和骑行队骑行。图/徐巧丽
为了拍视频,她比以往更经常上县城里转悠。在安阳的街头,卖西红柿的小摊贩认出了她,要和她合照;在人民公园,一个60多岁的大爷要看她割麦子。半年没去过的卖菜摊位,卖土鸡蛋的王奶奶拉着她问,“都说你发财了?不种地了?”
秦士芳急忙辩解,“我又没带货,还是搁家里种地。”王奶奶转头就走,“我不信。”走出几步远,又回头强调了一次,“我不信。”
被选中的三姐每晚10点,网红作家大冰的直播间都有七八千人观看。观众好不容易连上麦了,问题千奇百怪——怎么修坏掉的床?要不要去堂弟的店里帮忙?有自媒体总结,他们大多是三四线城市里“沉默的大多数”,什么事想不开了,拿不定主意了,过来倾诉倾诉。
去年8月底的一个晚上,“想去祖国的大好河山”,一条“三姐”的留言在弹幕上飘过。三五分钟,“三姐”赶巧就连上了。一个60多岁的农妇,直播间稀罕的群体,轻声讲出自己的愿望,“咱们农村嘛,种完麦子就往南走,搁云南,西双版纳那儿转转,过过冬天,怎么样?”
这句话让那晚的连线视频爆火,全网开始寻找这位麦子阿姨——大冰说,她代表着我们已然老去的父辈,代表着我们曾经在田间耕作过的姑姑、婶儿、姨,甚至是妈妈。
“三姐”连麦的时候正是农闲,玉米收完了,白菜种上了,可以看短视频看到晚上11点。时事新闻,养生专家,还爱看云南的风景旅游。
三年前,孙子升上二年级的那个冬天,她就想出门旅游了。豫北平原的冬天是“蔫的”,麦子背着厚厚的霜,树杈子上落着雪花,人就呆在家里围着煤炭,后来是小锅炉,再后来开空调,大部分人会出门找点活干。那一年冬天,“三姐”开始想象,南方的冬天是什么样?有山有水的地方什么样?
她对出门进行了一番设想:卖菜的三轮车是大电瓶的,能走一天,还买了摆摊避雨用的帐篷,再带上家里的锅碗瓢盆。可准备妥当了,又有孙女了。
孙女比孙子不好带,性子比较急,更喜欢出去玩。早上,她要做饭,喂奶,下午再带上奶粉带孩子出门玩,等孩子睡了,才能把锅碗瓢盆洗了,把地拖了,把衣服洗了,日子过得紧巴巴,休息的时候非常少。
去年11月初,她连麦之后,被短视频平台找到时,正在县城卖白菜的摊位上。有个电话打了两次,三姐接起来,“你在网上火了,人家都叫你麦子阿姨,都在找你。”
对方告诉她,她讲的那句“种完麦子往南走”被作成画,写成诗,做成网络歌曲。大冰发布征集令,要给她找一份在西双版纳的工作,让她打工换宿,还提供往返机票。短视频平台请她吃饭,在酒店给她过生日,买蛋糕,从大数据中捞起真实的“三姐”,支持她出门旅游。
农闲了,在家打蚊子的“三姐”。图/徐巧丽
丈夫李吉明却是第一个反对者。他把合同仔细看了两遍,记得合同上写,一切行动都要经过对方同意,否则罚款好几十万。合同期限是半年,过了半年,对方有权再延长半年,还可以无限期延长,“这不是你的一生就埋在这里了?”
李吉明高中毕业,掌握点知识,西双版纳是个啥地方却不晓得。先去手机上搜云南,再搜昆明,西双版纳在边境,这下不得了,“要被骗去缅甸搞电诈?”
他给秦士芳的几个姐妹打电话,六兄弟姐妹里她排行老三。大姐在家里带孙子,觉得这不安全;四妹在家养奶牛,出门就会晕车,不敢想这得多远;五妹在上海做保洁,一开始也不想让三姐去。所有人都劝,三姐就是“非去不中”。
在县里做医生的儿子表态了,不同意妈妈出门,家里出啥事儿,连照应的人都没有,更不好意思让她坐别人买的飞机去旅游。
唯一支持的人是四妹夫贵平。贵平给李吉明做思想工作,给三姐儿子做思想工作。用DeepSeek查去西双版纳旅游要多少费用,还看了西双版纳的天气,给三姐发过去,“扑风冒雨,必须要考虑身体,毕竟年龄在那儿放着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,有时也很无耐(奈)。”
贵平是高中生,本想报考音乐系,但高考差了几分,喂了四十年奶牛。早上4点半起床挤奶,下午卖奶到6点。这活太绑人,一般出门不超过20里地。最近几年,他还完了买奶牛借的贷款,不愁经济了,才报了个乐器班,买了葫芦丝、箫和笛子,学着吹《二泉映月》。
谁不想出去见见世面?谁想整天就守着这二亩三分地儿?三姐比他大几岁,年龄再大了,想走也走不了,他觉得这个机会,就好像“自己没有圆的梦,人家去圆了。”
临近出发的前几天,李吉明还在想办法。他把老伴身份证藏在了高一点的地方,老伴也有对策,“我办临时身份证也能走。”他急了,“你走了就没有家了!家重要还是去那儿重要?”就这也吓唬不到老伴,“你说啥我都要去。”
真正让三姐非去不可的原因,是左腿膝盖患了湿疹。之前她在一家工厂干保洁,累着了,如今一年比一年难受,早上睡醒也酸痛,去医院看说是老化。三姐心里想,得赶快出去。
临走的前一晚,丈夫终于同意了。但有条件,不能暴露自己家的位置,还互相约好了暗号——要是遇到啥危险,她就说“我很好,没有啥危险”。听到这句,丈夫就给派出所报警。
流量就三个字:在路上去云南之前,秦士芳把ID从“三姐”改成了“麦子阿姨”。出了安阳以后,她才真正知道这个标签意味着什么。
从安阳到昆明,由大冰的朋友「废材」护送,他发了个视频,“麦子阿姨后续第一站记录来了”,收获81.2万赞。李吉明也看了视频,“岁数不大的黄毛,给她扛被子,拿行李,还请她吃东西,这下放心了”。
之后从昆明到西双版纳,另两个博主骑摩托载着她,再由西双版纳的一个博主接到民宿。这一路,每人都涨了几十万粉丝。
在民宿,秦士芳一天上10小时班,两班制,休息的时候她就出去玩,傣竹园、森林公园、佛寺。走到哪儿,都有手机对着她。她才知道还有“流量”这个说法,跟种地完全两样,“噌噌往上涨,但又看不见摸不着”。
那段时间,全网都在呼叫“麦子阿姨”。出发前,老家文旅局就给了任务,让她在自家转转。到了西双版纳,有人要给她免费摆摊卖烩面,酒店的私人经理,饭馆员工,房产中介,都在邀请她,“愿做您的帐篷”。
理发店的Tony、美甲店的小哥,要给她免费做头发,纹眉毛。按照学来的新理论,秦士芳明白了,“谁拍我谁有流量。”
新店开业,她也被拉去撑场面。秦士芳记得,一次参加饭局,“一个裤头都要好几千的老板,上来就说,麦子阿姨我好羡慕你,我是你的粉丝”。她坐在角落,听这些人聊买房子,花了几十“个”,几百“个”——“个”是啥单位?直到有人拿她开玩笑,“麦子阿姨接广告也有几个”,她才知道,“个”是万的意思。
被邀请参加央视春晚,又是一波噌噌上涨的流量。之后,她成了广告的宠儿,几家互联网大厂找她拍广告,她去了辽宁、上海,又回到云南。
秦士芳在云南过的傣族年。讲述者供图
外头的世界跟西辛安村真不一样,天天都不一样。就拿花和树来说,安阳的树多,梧桐树,国槐,豫北平原上,不是黄的,就是绿的。云南的花多,她认识了鸡蛋花,五瓣梅,五彩缤纷。
年轻人对她尤为热情,“想不到你们这年纪还有出来的想法。”打车碰到的小姑娘开心地告诉她,“我也带我妈妈来大理旅游啦!”
有些小姑娘干脆认她当干妈。“大女儿”长得大眼睛,一米七几的个子,秦士芳去取快递,上来就认出她,你是麦子阿姨?她跟儿子差不多大,40多岁,未婚,和秦士芳倾诉,“我也没有妈妈了。”她给秦士芳买了一套傣族衣服,包了1000红包。
还有个“女儿”在洱海边认识,短发穿西装,送了两件棉袄,邀请她去家里住了两三天,亲手做江西菜,讲起自己离婚,带孩子的经历。
“女儿”家的小院是自己设计的,附近是菜田——终于到了秦士芳的主场,她去看云南农民种土豆,生发感慨,“我们河南的土豆刚种下,人家种的土豆已经绿油油的了”。走到香菜地,“怎么是一簇一簇的?我们都是种的密密麻麻的。”这些她都拍下来发给家里人。
云南的香菜。讲述者供图
秦士芳种了半辈子地,觉得种地靠管理,“苗儿该拢的时候拢,不拢的时候它就长窜了。”对粉丝,她觉得也像苗儿一样,多施点儿肥,多浇点儿水,比如给“女儿”们买点菜,过年发个400块的红包。
种地靠天吃饭,老天不叫你收,一场大风也能刮坏。今年3月,流量的大风也刮到大理——有个广告想让秦士芳去泰国,护照都办好了,广告方突然不再继续,对方意思是,流量下降了。秦士芳又上了一课,“流量它掌握不住。”
这时候,一个做运营的朋友方圆给她列出了两年的账号计划,强调说,她的流量就三个字,“在路上”。他让她考驾照,未来五年都在路上;维持人设,穿衣服不要那么贵气,保持乡土的穿法,流量就会一直有,“毕竟一句话感动了这么多人”。
方圆之前做的是后端运营,付费的底层逻辑摸了个透,也相信短视频可以改变大多数人的命运,但没做过自带流量的纯达人赛道,他希望能在麦子阿姨身上实践理论知识,“像养孩子一样养这个账号。”
他在春晚前跟秦士芳达成合作,觉得她是“天生的达人”“比苏敏还苏敏”。在他的规划下,麦子阿姨从大理回安阳老家没有坐飞机,而是自驾三天,2200多公里。
在秦士芳的印象里,这是第三次“流量噌噌往上涨”的时候。他们原本打算,回去就考驾照,直接“往外走、往北走。”
“也是唯唯诺诺出去看看”天还没亮,秦士芳吃过早饭,走的时候拿了点花卷、馒头,还有咸菜,走上西辛安村连着的301省道。坐上汽车,到火车站下车,买一张坐票,晃悠两三个小时——这不是64岁的秦士芳,而是20岁的秦士芳,第一次离家出走。
她要去郑州二十里铺,学裁剪。1981年,她对郑州一片空白,只听表姨说郑州很大,到那儿一看,裁缝班在郑州农村,“没有几台缝纫机,睡觉也是男的一个大炕,女的一个大炕”。她想着好歹学个技术回来,开个裁缝铺。
走的时候没跟爸妈说,也没跟大姐和二哥说。直到让大姐寄点儿钱过来,家里才知道她去学了裁缝。那一阵儿时兴裁缝,她听收音机里的广播知道的,心里谋划了起码两三个月。
收音机小小一个,银色的,连着长长的天线,是秦士芳通向外部世界的启蒙老师。
她白天要挣工分,闲下来也要纺布织布、纳鞋底,做被子,只有晚上的时候,她打开“小喇叭”,调到喜欢的新闻,哪一年修路了,哪条路挖到什么程度了,“只要是新闻报出来的,都是你不知道的事儿。”
“郑州二十里铺裁缝学校招生,男女不限,有工厂对接可直接上班。”秦士芳仍然记得,当年收音机里这么说。学裁缝是她为自己想到的一条路。她小学五年级就辍学,在家照顾三个妹妹,生活就是喂猪、喂鸡。十几岁懂事儿了,老是觉得不甘心,“还是希望读书,不愿意就这么安排工作。”
裁缝班学了两个月,她把老师也带了回来,办班教学生。这样做了两年,有次在家捻棉花,左手出了事,就不办了。那时别人都找婆家了,生孩子了,村里和家里都开始催。李吉明是小学同学,次次考100分,她觉得识字多,有文化,就结了婚。
秦士芳和李吉明的结婚照。图/徐巧丽
李吉明喜欢下象棋,往往是对方的车和卒先过河,他再出击,“最重要的是守住自己的将帅。”对他来说,家就是他的将帅。存钱不就为了老了生病能有个保障?他管账理账,生活仔细。还爱搞些小发明,铁锹上头装个漏斗,化肥顺着铁锹管滑下去,不用弯腰施肥;犁地的前头装个小轮子,省了力气。
秦士芳嗓门大,性格强,不认识的字去请教李吉明,他会不耐烦,“这不都教过?”后来两人开小卖部,进了一批新华字典,秦士芳拿了一本自己学,翻到书页都断了线。
两口子意见不一致,李吉明主张谁有道理听谁的,但有时讨论着,秦士芳就生气了,“你哪里有做得不对?你都对,你全家都对。”吵架的时候,李吉明出门和人下棋,秦士芳就骑上自行车,出门转一圈。
秦士芳喜欢往外跑,六姐妹都是知道的。家家户户的屋顶连着,方便晒麦子晒玉米,大人们在屋顶干活,“三姐”就喜欢从这个跳到另一个,往远了看。
她在301省道边长大,爷爷在路边开车马店,后来爸爸又在对面开了一家农村饭店。来吃饭的都是拉煤车的,收废品的,或者赶路的菜贩子。有次遇到一个变魔术的,变出一把辣椒,一个个吃。对秦士芳来说,“外头”就是省道连通的两边:山东、河北,能带来不一样的人。
自行车是她的必需品,生气的时候骑着出去转,看看外头有什么不一样。但是,路上遇到男青年吹个口哨,或被人骂了脏话,她也害怕,光走大路不走小路,“也是唯唯诺诺出去看看”。
唯一一次不想出去,是儿子一岁的时候。她当时把孩子带着,去太原做生意,看到新闻上有人把小孩拐走,让他要饭,她吓得赶紧回了家,一直到儿子7岁上小学。等到儿子当了父亲,她又带孙子孙女,洗坏了一次儿媳妇的衣服,儿媳妇就不高兴。
64年,她的人生“中心”就是家。前屋是厨房和卧室,后屋给儿子结婚,再加上一间小卖部。平时,她出去晾完衣服,再擦灶台,有时帮小辈做件衣裳,丈夫躺在小卖部柜台里刷手机。农闲了,做饭就是一件大事,蒸个馍馍,做个菜卷卷,可以忙前忙后两三小时。
出门就是去县城,骑着三轮去卖菜,大街有城管,她老往热闹的小街钻;安阳桥的河滨公园、洪河湿地公园她也熟悉,分别是下午带孙子和孙女打发时间的地方。
她自觉地把对外界的好奇压下去,不去想。“你有一个家庭,有孙子孙女,儿子,媳妇儿,得为这一个家去着想。”如果向外走和家庭有比重,她觉得向外走只能占“一两分”。
秦士芳的柜子。图/徐巧丽
通过家里的电视,也可以看“外头”。
秦士芳年轻时就是如此。时机得巧妙。儿子在写作业,她不能看,耽误学习;作业写完了,遥控器就不在她手里了,儿子要看会动画片;晚上睡觉,为了不影响儿子,也不能看。只有中午农闲了,能看一会儿新闻,香港回归了,伊拉克打仗了,网购也是在电视上看到的。
电视里头介绍网上买东西哪儿好,她屋里有一柜子,放着空气炸锅、豆浆机、智能电饭煲,都是在网上买的。秦士芳爱赶时髦,只用过一次老年机,摔坏之后,让儿子给她买个“带屏幕的”。
如今上了年纪,能消磨时间的变成短视频。孙女一岁的时候,她关注了一些云南旅居的博主。“辽阳北台子苗圃/云游天下”开辆五菱宏光从东北到云南,全天直播,她有空了就跟他连麦。“新民朱姐”开三轮电动房车,秦士芳私信问她怎么打工旅居。
还有一个在云南的东北博主,秦士芳给她点的红心最多,去年2月她连上麦,问云南房费她能不能承受。后来她做了这个博主的直播间管理员,在视频里看到云南的火龙果开花,她对博主表白,“我内心非常喜欢你,要带着我看世界。”
后来,大冰开摩托旅行的直播间被算法推给了她。秦士芳一看,这不是儿子小时候看的山东电视台主持人?在她的设想里,搁山东走228国道,沿着海就能到云南。
出门就是麦子阿姨,回家就是秦士芳如果说这趟旅行真正改变了什么,那应该是眼界开阔了,不能一辈子种地,得“撵着时代走”,秦士芳说。她回来第一天,四妹夫贵平还是在喂奶牛,她让贵平也拍拍自己的日常。
因为一次广告需要,她成立了“西双版纳麦子阿姨”公司。那段时间,做运营的朋友方圆每天都在给秦士芳上课,提升她的认知——“你走出来那天,你就是麦子阿姨,当你回到家,你是妻子,你是一个母亲,你是秦士芳。”
方圆给她选择,“如果你想做秦士芳,回家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,把饭做得漂漂亮亮。如果你想做麦子阿姨,那就要从里到外去改变,改变你对麦子阿姨这个形象的理解。”
但在投流问题上,秦士芳开始害怕,听人说“流量是个无底洞”,不太愿意掏钱,最后两人也没有签约。
秦士芳打算按照自己的理解,继续做“麦子阿姨”。短视频平台的合约今年5月到期了,不再续约,她开始物色家里的小辈,经营账号。
侄女性格外向,办事利落,在商场卖化妆品。但侄女没那个闲工夫,卖化妆品也能挣一个月五六千。
37岁的外甥女,人比较实在,在太原卖卤肉,生意不太好做。她给外甥女打电话,“你现在生意咋样?”外甥女也愁,一天只挣一两百。她答应下来,还有一个原因,儿子女儿放暑假,这份工作灵活自由,白天拍得差不多了,就可以回家接孩子。
秦士芳给她推荐了一位指导老师——跟拍西双版纳的纪录片导演。导演说,“你看人家(自驾游博主苏敏)都做得这么好的了,阿姨要是做的话肯定也可以。”
外甥女给秦士芳拍视频。图/徐巧丽
外甥女许瑶也没想到,她姨这么有网感。坐飞机,向空姐点咖啡,随口就是一句“苦点儿吧,以后就不苦了”。面对媒体的提问,她姨又出金句,“你们村的路如果是光滑的,不粘脚的,就应该多走走不光滑的路”。
那段时间许瑶和秦士芳都信心满满。秦士芳给外甥女买了新款苹果手机,收音器,还花了2000,报名了一个剪辑班。除了教基础的拍摄镜头,也教流量规律,比如爆款的标准,怎么选个好的赛道。
具体到麦子阿姨的情况,热度已经过了,怎么样维持流量?老师让她们去关注麦小登,走三农赛道。指导完了,不忘邀请秦士芳,拍个视频宣传她的课程。
结合苏敏和麦小登,许瑶总结为,“出去就是旅游博主,回家就是三农博主”。老师还建议许瑶,用麦子阿姨的口吻写文案。什么是麦子阿姨的口吻?有次去呼伦贝尔上节目,许瑶想到一句文案,“收完麦子我就往北走”,这条流量不错。
其它视频反响平平。秦士芳喜欢拍“早上几点起床了,去菜市场买菜了……”许瑶觉得这是流水账,要有主题。秦士芳又觉得,许瑶只顾着孩子,对拍摄不上心。丈夫成了秦士芳的第二助手。
李吉明态度的转变,源自一次突如其来的流量。秦士芳在外旅游,有次两个初中生来小卖部偷钱,被监控抓个正着。他把监控发到网上,结果有20万阅读量,派出所妥善处理了此事。现在,他也给秦士芳拍一些做菜做饭的镜头。
秦士芳做馍馍,李吉明拍摄。图/徐巧丽
但流量一天不如一天。6月29日这天,秦士芳弯腰拔玉米苗,许瑶的镜头对准她。一组镜头要拍三四个,天气闷热,一排排麻雀从玉米地里飞出来,秦士芳拔玉米苗的时候,浑身都汗湿了,她招呼许瑶,“过来拍拍我的汗。”
还是那片很多媒体拍摄过的麦子地,如今只剩下麦茬,新种上了玉米苗,长到小腿高。这时节的工作,是拔掉长得密、长歪了的玉米苗。拍视频前,两人刚用一下午除完了地里的杂草。有一种大屁股草,长得强壮,很难拔。更强壮的,要属韭菜,春天的韭菜鲜嫩,但五月的臭韭菜就不好吃了,被误当作大屁股草拔掉几根。
拍摄结束,素材还是凑不够一期视频,许瑶为更新发愁,蹲在田埂上点开苏敏,点开麦小登,想要寻求一些改变。“网友想看到麦子阿姨啥?”再点开麦子阿姨的粉丝画像,显示人群主要是男性,喜欢看李子柒、董宇辉和大冰。许瑶搞不懂了,“还是大冰的粉丝在看麦子阿姨?”
(文中方圆、许瑶为化名股票什么叫杠杆。)
发布于:北京市